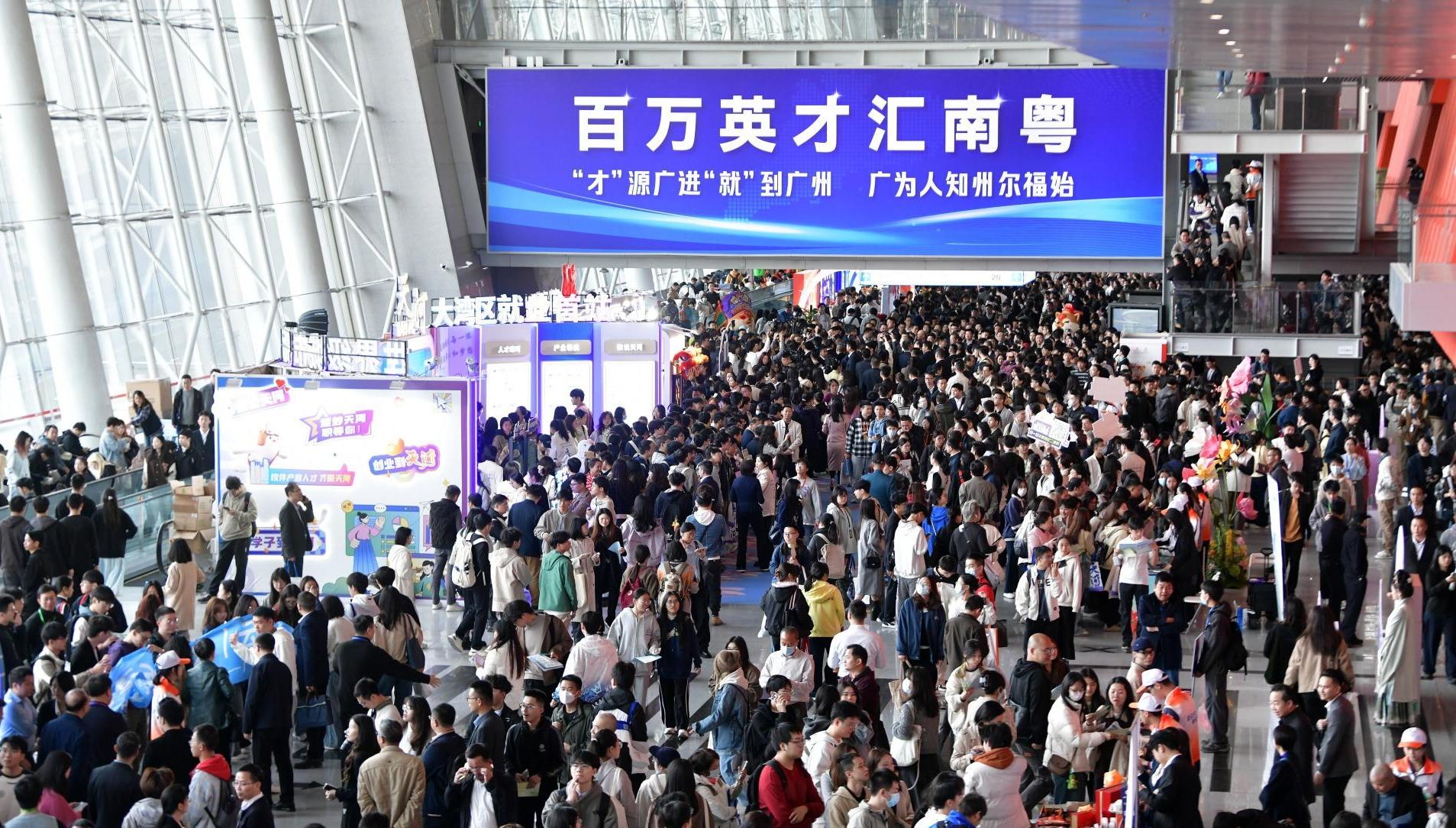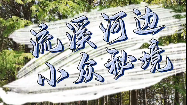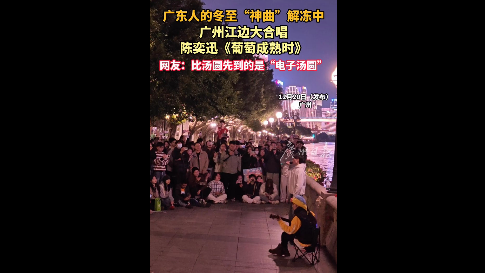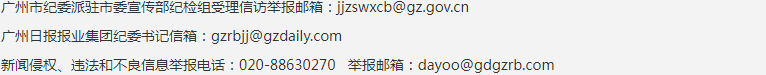很多年前那个炎热的下午,当我读到加西亚·马尔克斯的《百年孤独》中,美人儿雷梅黛斯随着一阵风,抓住一幅雪白的床单升上天空,魂归故里,思接千载那种充满了魔幻色彩的情节时,我心想:像这样自由地放飞作家的想象力,让现实、历史和梦境无缝对接的情节,恐怕很多作家是很难驾驭的——也的确如此,在我这些年的阅读经验中,很多作家在他们的创作中,对马尔克斯的模仿和致敬,时常显得生硬和造作,这无疑加固了我对这一已有判断的确认。但当我读到张梅的新作《烽火连三月》中,赵连如老太太坐在一块疾走的乌云上,穿行于广州城的上空,梦萦峥嵘岁月,心系旧时故人,在现实与过往岁月中自由地切换穿梭的场景时,我知道,我错了!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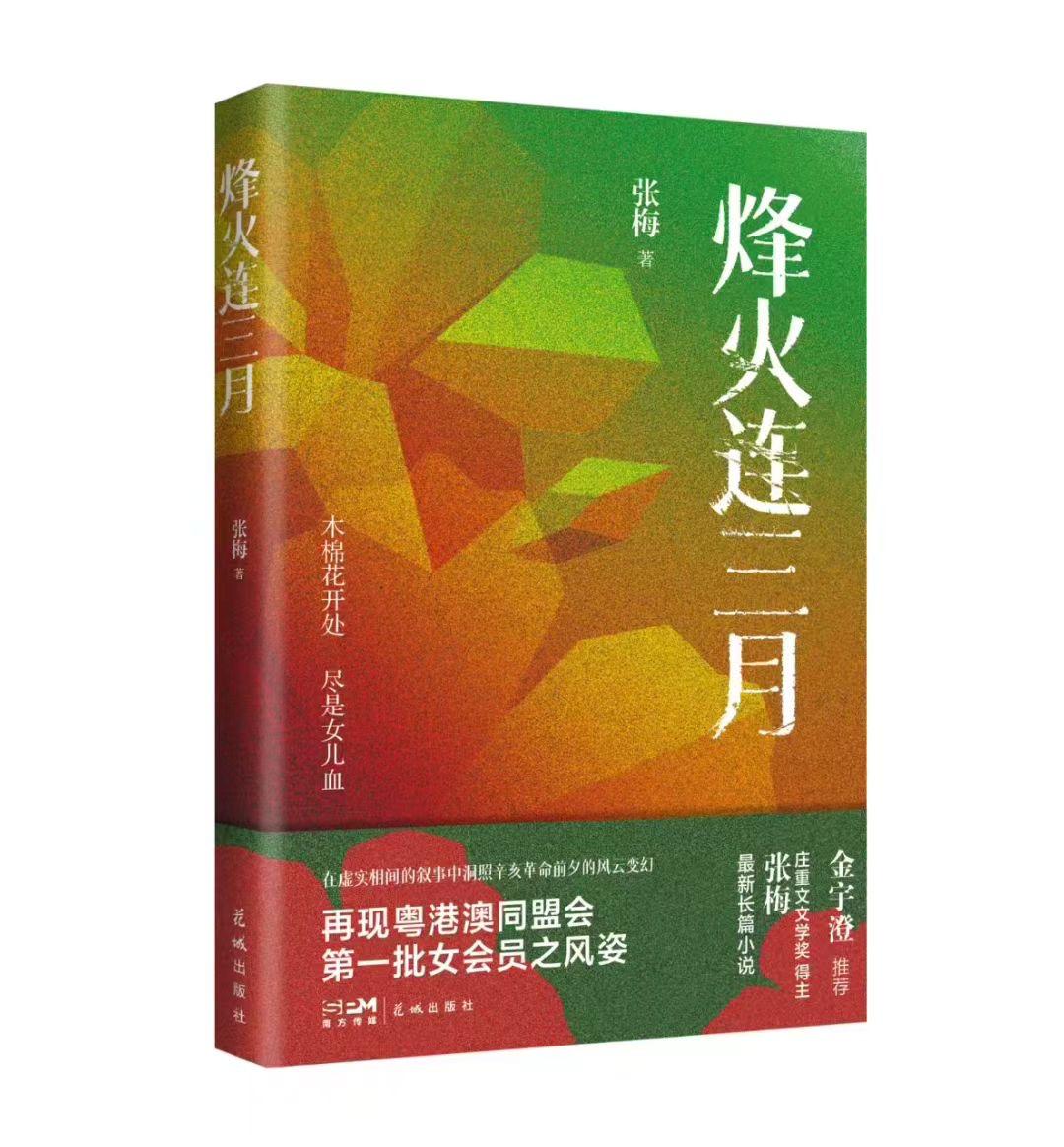
《烽火连三月》是一部讲述辛亥鼎革前夜,粤地最初一批同盟会女会员在省城(广州)进行的一次未遂剌杀行动。乍一看书名,给人的印象这是一本讲述战事频仍,岁月倥偬人生故事的小说,然小说中的主人公,即便不是大户人家的千金小姐,也是衣食无忧的时尚女性,她们参加“革命”的缘由各异,但对一种“新世界”“新生活”的向往和追求却是相同的。且小说的作者张梅并不打算或并不擅长让她的主人公们,在烽火连天的岁月中映射她们“战斗中的青春”,而是选择了让她的“女人花”们,在万丈红尘中摇曳绽放,暗香氤氲,这才是张梅所擅长和谙熟的。
大约二十年前,哈佛大学的李鸥梵教授和著名评论家李陀路经广州,因李教授早年时曾客居上海,张梅便在一家名叫“上海往事”的饭馆作东请客,宴请两位远道而来的客人。席间,李教授在感慨那家饭馆本帮菜做得“地道”的同时,也惋惜在后来的中国当代文学中,再也难寻像张爱玲那样洞悉现代都市风情,并在其作品中淋漓展现的作家。话音刚落,坐在一旁的李陀接过话茬,他对李教授说,坐在你对面的张梅倒是一位颇有可能续写张氏都市风情的作家,“在现时的中国作家中,真正熟知都市生活,并能领略其中精髓的人极少,张梅算是一个。只可惜的是张梅不够勤奋,作品太少。”李鸥梵闻言大为兴奋,隐隐也对张梅的创作有了某种殷殷期盼。只是一向过得闲散又洒脱的张梅,并不在乎那些殷殷的目光,一如既往地飘逸洒脱,但这绝不意味着张梅把她最钟情的文学创作忘诸脑后。这不,张梅的长篇新作《烽火连三月》,先是在被多年不刊登长篇小说的《上海文学》破例连载之后,又被花城出版社隆重推出。
《烽火连三月》在张梅的创作生涯中,无疑是续《破碎的激情》《游戏太太团》之后的又一力作。这部小说是张梅以往的创作中鲜有涉足的历史题材,而且还事关“革命”,这可是张梅自己给自己出了一道“难题”——自从从事创作以来,张梅对如何进入“宏大叙事”,一向是“敬而远之”。对付诸如辛亥革命这样“宏大”的历史题材,我以为张梅也会像其他类似的写作者一样,艰难费力地在史料故纸中,整理梳耙,然后吭哧吭哧地上“史料”——通过她从故纸堆里“打捞”出来的线索、记忆,编织她的人物、故事,可是我又错了!张梅四两拨千斤般化解了横亘在她创作中的这一难题——她把她小说中的人物和故事,安放在她所极为谙熟的,珠三角地区的世俗生活场景(相对于革命而言)中,慢火烹煮,精心调制,使之香气缭绕,诱人探究……更让我惊异的是,张梅居然娴熟地把南美魔幻现实主义的创作手法,嫁接在了她的新作中,非但不让人觉得突兀违和,反而觉得贴切自然,文思灵动,神采飞扬。
这部小说中的主角和其他的一些人物,无疑是有着历史和现实中原型的,但张梅在创作的过程中,犹如《封神演义》中太乙真人对哪吒脱胎换骨的再造一样,张梅对这部小说中的人物也掰开揉碎,进行了重塑。这部小说的主线,大部分时候,还是围绕着主角赵连如参加“革命”前后的时间线来展开的,虽然在那场“革命”(刺杀)行动中,赵连如整个人都处在一种“矇查查”的状态中——既不清楚行动的具体内容(行动的具体时间、地点等),也不太清楚自己所担任的角色、任务是什么,但是她是这场行动的幸存者和记述者,这就足够了!

《烽火连三月》中的“烽火”,在我看来,指涉的并不是现实生活战乱频仍的景况,而是一场巨大的社会嬗变过程中,烤炙着社会人心的变革之火,正是这一“烽火”,焚毁了延绵千年的帝制。而在成为烈焰冲天的“烽火”之前,那一切都只是并不起眼的微光烛照,譬如在日常生活中出现的“新”物事——赵连如出生地毗邻澳门的村子,不知怎么地,突然就办起了免费的教会学校,让她有机会迈进了学堂,从此改变了她人生的轨迹。要不然,作为一个轿夫的女儿,她的命运和她十八岁就嫁人成为农妇的大姐不会有什么两样。又譬如地主陈四眼的表弟,在秋风起时,从澳门带来一部有两个轮子的“东洋车仔”和洋酒白兰地,来探视其表哥,他们边饮着传统的广东米酒,品着白斩鸡、燉禾虫、豉汁蒸白鳝,边议论着究竟是要支持康梁还是孙文——这在当时的珠三角,却是寻常的乡间闲聊。在这部小说中,张梅正是通过这种不动声色,且神形兼具的叙说,让这些并不打眼,但已然或明或暗地运行在帝国统治缝隙中的“地火”,第次蹿起、蔓延、升腾,最终成了燎原之势。
小说中彼时的省、港、澳一带,虽说正处于鼎革的前夜,但当“革命”的烈焰冲天而起之前,寻常的百姓人家大都并没有多少先知先觉,他们总是一如既往地演绎着自己的“清明上河图”。而对“大变局”前夕中国最早出现的都市圈生活场景、人生百态的细微捕捉和精彩描摹,正是小说《烽火连三月》的精华所在,正所谓“众里寻她千百度”,“那人”却在人间烟火处——描写这种都市的世俗生活,最是张梅所擅长和谙熟的。说到珠三角一带的世俗生活,“吃”自然是要排在第一位的。在这部小说中,作者对“吃”的记述和描写,不厌其烦,精益求精。我们不妨先看看,书中自认为是“美食家”的斗门地主陈四眼家宴的一道菜——燉禾虫,其烹制过程,小说中的陈述,简直到了令人发指的教科书级别。
先是备料:
禾虫两斤,鸡蛋四五个,杭椒一两,蒜肉一两,油条二根,生油二两,肥猪肉二两或油渣二两,古月粉(胡椒粉、橙皮切成小粒少许,瘦猪肉一两,浙醋两小碗。
然后是烹制:
各项物事备好后,先用清水将禾虫渗透,再将禾虫捞起。按照此做法,重复三次,以去除禾虫的泥味。然后用干布吸干水分,放在瓦砵上。再将生油倒入,加入蒜蓉,使禾虫爆浆,然后用胶剪剪之。后放入鸡蛋,肥肉切粒,油条切片,食盐少许,古月份,陈皮粒,杭椒粒。各种配料放入,搅匀。隔水炖约两小时。后取起,放入瘦肉,再将禾虫放到炉上烘约30分钟。
这简直和《红楼梦》中,王熙凤向刘姥姥炫耀他们贾府烹制茄子的一道菜(茄鲞)的做法有得一拼了。
小说中对当年南海沙头镇,老饕们对当地一种叫鱼生的美食的痴迷垂涎,亦有极生动精彩的描述:每年八九月间,秋风既起,菊花上市,这些人不动声色地从四面八方慕名涌来,当白花花的鱼生片摆上桌的时候,一声号令,装着炒花生、柠檬叶丝、酸荞头薄片,蒜片、姜丝,还有炸香白芝麻、油炸鬼薄脆、花生油等各色令人眼花缭乱的佐品纷纷上桌,老饕们眼露精光,嘴角流着口水,(甚至)纷纷跪倒在与生鱼片下,用普洱茶来净手,然后再往身上洒柠檬水,口中念念有词,最后把生鱼片拨进自己面前的碟子中。路途近的,就大饱口福,喝了当地米酒,唱着咸水歌坐着龙头船,趁着明晃晃的月色回家;路途远的就等肚子把晚餐的鱼生消化了,再进行另外一场鱼的盛宴。
很多年之后,坐在云朵上在广州城上空巡游的赵连如,最让她流连忘返的竟然是那些如数家珍般的饭馆和菜肴——华北饭店的煎饺子,惠如茶楼的干蒸烧卖,回民饭店的沙琪玛,菜根香的罗汉斋,太平馆的牛扒……小说中写道:“如果不是当了革命家,她应该会在澳门开一家饭店或者甜品店,做一碗杨枝甘露。想当年她还是少女的时候,就能做一手好菜,特别是红烧乳鸽。冯雪秋对她说,在枪林弹雨中,他闻到了她做的红烧乳鸽的香气。”
如同《百年孤独》中的许多人物在小说中会反复出现一样,在这部小说的最后一章“芳岭永续”中,冯碧玉和陈佩儿这对“故人”又在21世纪20年代的香港“相遇”了。这两个年逾花甲的同龄人,一个居住在香港,一个生活在内地,素昧平生,按说她们生活的时空很难有什么交织之处。但巧的是,这俩人都喜欢唱歌,在一个歌友群里,她们“认识”了(冥冥中的“定数”)。小说中写道:“唱歌群里基本是唱传统民歌的多。一天她(碧玉)听到有人用粤语唱雷安娜的《旧梦不须记》,虽然一听就是没有经过训练的,但唱得慢条斯理,很忧愁。那种忧愁打动了她,她一下子记住了这个声音。唱歌的就是佩儿。”于是,她们约好了在那年的圣诞节在香港见面,然后一起去听一个粵剧堂会,堂会演唱的剧目叫《大闹广昌隆》,听说有一对马来西亚的姑侄要来,一对年轻夫妇是从澳门过来的。“还有广州来的一个戏班老板,姓林,有一门绝门功夫,可以像女人一样裹着脚,踮起脚尖在舞台上做武打。还有一个江门唱木鱼的,是瞎眼的”……当年参与刺杀行动的相关角色又在香港“相聚”了。更为神奇的是,当碧玉在酒店大堂等着和佩儿见面的时候,“一个瘦削的年轻男人走了进来,他的穿着有些奇怪,头上是一顶上世纪初的白帽子,带着一副溥仪式圆墨镜,穿着一件唐装长衫,像个电影里走出来的人物。”时空在此似乎出现了错位。
小说的结尾,呈现出了一种开放性的结构,使得小说的文本延伸出了无穷的想象空间,并显得意味深长——那些已然逝去的先行者们又在另一个新的时空中再次聚集叙谈了。是的,也许那些先烈们从来就不曾在我们的生活中远去,他们一直生活在我们身边,注视并激励着我们前行,而那些曾经承载着我们过往和未来的梦境,也一直会陪伴着我们——“旧梦不须记”,也不会忘,它是我们今生或来世的路标!
文、图/文能
广州日报新花城编辑:吴嘉丽